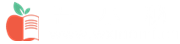老屋土炕散文
老屋土炕散文 我家老屋散文
本文由吾小秘【www.wxiaomi.cn】会员分享,供您参阅。文内整理了1篇相关范文,平均每篇5580个字,阅读大概需要13分钟。
下面是范文网小编整理的老屋土炕散文 我家老屋散文,以供参考。

老屋土炕散文
一、老屋
故居说是故居,其实并不是我祖辈世居于此的地方,而曾经是别人的旧屋子。
曾氏是村里的大户。往往,什么东西一大,外人看上去很壮观,很有势力,其实内部,早就分化得厉害,也分野、分生得厉害。高祖兄弟四人,我至今说不出高祖的其他兄弟的名字,也弄不清村里谁是他们的子孙,就像我四十多岁了,不知道曾氏的祖坟到底在哪里一样。我的祖父也兄弟四人,下来我们这些没出“五服”的本家,婚丧嫁娶一般都正常走往着,但各自另家分院。
我的祖居其实就在有两棵古柏树的三观庙前,现在由八十多岁的二叔他们老俩口居住着。我最早记得这处院子,是祖父去世那会儿,两三岁的我,风葫芦般在各屋子乱跑,突然就奇怪地发现,祖父端坐在堂屋中央,身上围着块刺眼的白布,四叔给他理发推光头。不知又过了多久,就看见父亲大步流星地赶来,一进堂门就裂开嘴“爹呀,爹呀”好笑地嚎叫。那时,我什么都不懂,好奇地追随着父亲进东屋看,只见祖父已经闭上眼睛,身上苫着暗色被子,一动不动地躺在后炕的门板上。父亲等人围着,顿足捶胸地哭。
祖居倒是有几间房,但父亲兄弟几个一分家,就显现出诸多困难和矛盾。作为曾门长子,为了兄弟间家庭和睦,一九五九年末,正赶上大同市外科名医李万禄要举家迁往市区居住了,也就是要把他那个嘴头特别厉害的“二老虎”妈要接走了,这处院子就由父母举债80元买下了。搬家那天,二哥正巧出生。因此,这里就演变成了我们的故居。
当初,故居院里只有两间很小的房,一里,一外,也即住房一间,堂屋一间。直到今天,母亲都住在这间小屋子里。尤其是冬天,她觉得暖和。这两间房几乎都是土质的,后墙有厚厚的土板墙挡着西北风,内侧全都用土坯垒砌。房顶是黑黑的杨木椽檩,早些年,连个“仰承”都没有,烟熏火燎,雨洇气蒸,自然就看不出木头的本色。映像很深的是,大约在襁褓中的我,睡醒或溺屎后,发现没有亲人陪在身边,就狠狠地哭,哭到屋顶黑黑的椽子,像流水般哗哗哗哗地向远方流去,直流到我无望地再昏昏睡去。后来,大哥学了木匠,就在屋顶上加了木撑档,用旧报纸糊了顶棚,这才有了“仰承”。有了仰承,晚上睡觉却更不安稳了,房顶掉土,不仅仰承经常嘣嘣嘣嘣乱响,有时哗——地一下,一大块土块就轰然落下,砸塌仰承纸,打到人身上或者哪里。因此后来,父亲和大哥又在仰承档上,堵了几块比较耐实的席子。这样一来,土是掉得少了,但总有老鼠在上面窸窸窣窣低音炮似的来回跑。
两间房子的西边还有一个更小的堆放物品的小房,后来,小房在某个晚上失火烧毁了。烧毁小房没什么可遗憾的,又没连累住房,可问题在于,姥爷留给母亲的一包陪嫁,即出身地主家庭的母亲,精心收藏多年的几件金银珠宝,在这次救火中被人趁火打劫,丢失了。这就让母亲一辈子难以释怀。每每述说起来,她的脸色就凝固了,眼睛也空洞了,陷入了一种应该清晰却毫无具像的追究着的激愤和苦恼。
大约有了姐姐或者我,家里人多住不下了,父母就在堂屋西边,即烧毁的小房位置上又扩建了一间。这间房就比较宽敞了。椽檩多半是松木的,砌墙的是烧砖的次品——不是土坯也不是砖的砖。这是一间故居最撑门面的房。大哥,二哥,以及我,结婚时,都是用这间房做的新房。现在,我们姊妹,我们这里管兄弟姐妹合称姊妹,都不住在故居了,和母亲住的小屋子隔着一间堂屋的这间房,就被母亲布置成平时礼佛的佛堂。
后来,这间房的西边,又续盖了一间木结构小房,我读初中的夏天,就独自住在小房里,身旁放着书包、桌子和煤油灯,什么时候醒来想学习,就围着被子,点亮煤油灯,坐在桌前,寂静而清远地在那遥遥的夜里,看书,做作业。这间小房平时家里就贮存杂物,地是用捡回的半头砖墁的,但七高八低,缺损严重。我知道它们这样的缘由,那是我曾经用夹子捕鸟,挖蚰蜒做诱饵的直接后果。奇怪的是,这间小房后来也因失火,烧毁了。再后来,母亲就把这片地,开垦成菜畦的一部分,种上了倭瓜、白菜、豆角及西红柿等菜蔬。
两间老屋的东侧,很长时间都是一片空地。我记忆中,这里一直生长着一片金格盏盏的高高的向日葵花。大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这里也续盖起正房一间,堂屋半间,和隔壁东邻人家的房屋就连成了一体。这间半房,我们家人几乎没住过,这是家里用来出租,每月挣一、两块“活”钱的重要来路。有人几次善意地提醒,叫我们住这东房,哪怕西面的房屋用来出租。因为农村特别讲究东尊西卑。比如一排房可以东高西低,但绝不允许西面的房顶高出东面。但也许是出于尊敬客人的缘故吧,父母根本不为所动。因而这间半房,几乎一直就留有人家,我们叫“住院儿”的。
也许就是父母对住客足够尊重的回报,这些“住院儿”的里面,有两户,以后就成为我家的贵人。头一位,当属胡成德叔。胡叔是从县里调到我们周士庄公社的`副主任。那时的干部,特别清贫。一两个简易四方的木板柜,三四个破纸箱,就是全部家当。我们两家人在一起同甘共苦生活居住了三年多。后来,胡叔离休于大同市二轻局局长。和胡叔家的交谊,我终身难忘。头一件,胡叔的两个儿子,小我几岁,但是我童年最要好的玩伴,许多我们一块“猴害”的场景,至今历历在目。第二件,胡叔的文采口才,是激发我爱好写作的重要心理诱因。胡叔在县上,曾当过新闻组长。在他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导下,我的一个本家哥曾新也喜好爬格子,后来任大同人民广播电台主编,获得过“范长江新闻奖”;二哥曾义也喜欢业余写些新闻报道之类,那些年,在大同矿务局工作的二哥经常把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拿给我看,念给我听。第三件,一九七七年,二哥首次参加高考,就以全公社第二名的身份考上学校。但因姥爷成份高,政审通不过,不允许走。危难之际,还是胡叔出面,二哥才最终得以脱掉农皮。此后,我们姊妹还多次“麻烦”过胡叔。
东房后来又有一户“住院儿”的,郭恒成叔。郭叔当着设在我村的县土产公司的经理。我村紧靠京包铁路和京张公路,交通运输条件特别便利。一九七一年大同县址移出大同市区,最初定址就在周士庄,因而这里有许多县属企业,比如县石油公司、县木材公司,县被服厂,县砖瓦厂等。郭叔的土产公司,对我家来说,简直就是雪中送炭。那时,我们姊妹全部上学读书,开销很大。父亲多病,不能干重活儿,挣钱能力有限,于是母亲一人顶着两份工,既要在一家小瓦厂做饭,还要捏压猫头滴水这样的瓦当,十个手指全部皴裂,经常血糊糊的。但纵使如此,家境还是入不敷出。姐姐因为家里没有八块钱学费差点儿高中辍学。于是母亲就经常和郭婶利用晚上时间顶着星星月亮,加班加点给土产公司装运货物,挣钱补贴家用。星期天的时候,我、姐姐及郭叔的女儿我的同学桂荣也经常参与其间。
幸运的是,除了大哥,我们其他兄妹四个陆续全都通过考学,如长了翅膀的松子,走出了故居,离开了故乡。于是,故居大多的时候,都苍老地静静地陪伴着我的母亲,看着她收拾屋子,看着她礼佛,看着她种养菜蔬,看着她精神矍铄不停地忙碌着。直到我们姊妹都回去,他那快尘封成雕塑样的外貌,像是猛地浑身一抖,又焕然出欣喜的气色,我们说,他听;我们玩,他看;我们笑,他笑。
老屋看上去很老很老了,以至于我们姊妹都看不过眼。于是,我们齐心协商,决定好好整饰一番。蓬瓦,吊顶,粉刷,修换门窗,油漆……老屋真的焕然一新了。
开工那天,母亲笑了,笑得特别开心,竟如孩子一般……
二、土炕
春节回故居跟老母亲一块过年,感觉真好。尤其是睡在那片土炕上。
那种沉沉的、酣酣的、静静的、暖暖的、深深地嗜睡,像是久违的让人迷恋的禅境,也像是幼年时母亲的怀抱,让我不自觉沉浸其中。是的,无忧无虑,无思无想,空明澄澈,我只想沉浸,也只能沉浸,一味地沉浸。
母亲就睡在炕头上,我紧挨母亲睡着。妻女们依次睡开。已经好长时间没跟母亲睡在一条炕上了。
平时,也常看望母亲,大多只是在地上站上一会会儿,连炕都不上;或者屁股跨在炕沿上,简单跟老母亲拉上几句,问候问候,炕沿都还没温热,就说要走了。母亲于是慌慌地忙碌,先是备水果,备瓜子,倒水,见我执意要走,就又忙着摘菜,装菜,并一再问我家里还需要什么,翻箱倒柜,忙里忙外,恨不得什么都给我拿上,连同,她那颗炽热的心。
这天是大年初一。大年三十晚上看晚会,午夜十二点忙着交年接神,母亲和我们都没睡好。初一就清闲多了。上午跟全村人到东南方向迎喜神,中午简单吃素,然后,就慵懒地躺在了久违的炕上。
正午的阳光透过玻璃窗,仿佛一张刚刚晒好的被子,暄腾腾暖烘烘的。炕呢,自然是一如既往的温热。这是四九节气,屋外,呵气成霜,滴水成冰,树枝都在瑟瑟发抖,人在外面一会儿就冻得受不了了。但此时,我就袒睡在我出生时的这片土炕上,四肢舒坦,浑身通泰。炕热和阳光更像是一双温热的手,轻轻的,悉心的,没有力道却力道恰好地给我做着全身的按摩,让我有些疲惫的身子放松,放松,再放松,一丝丝一缕缕的,抚去了那些隐约的沉重,酸楚,和疼痛。我恍如回归婴童。
直到太阳和炕不知疲倦、不厌其烦给我全身按摩得出了汗。我一睁眼,母亲的眼神一如阳光和火炕那样温热而慈祥地注视着我。
大概母亲想到躺在襁褓中的那个孱弱赤红的小小的我了吧。
那时,家里穷,我已经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。二哥下面的一个哥哥,因为营养不良,出生不到百天就夭折了。生活艰难得仿佛拖着一辆重重的上着坡的大马车,大约缰绳都深深地叩进父母的肩头肉里了。我的出生,自然给困境中的父母出了一道更大的难题。他们商量,要把我过继给也曾过继出去但已经相认了的王姓三叔家。三叔家有三个女儿,但没有儿子,正想抱养男孩。事情就那样敲定了,但临三婶来抱我走,母亲突然反悔了。她泪水涟涟,抱着吃奶的我毫不松手。最终,硬是把我留在曾家,留在这片我出生的土炕上。
我庆幸自己就出生就生长在这片土炕上,多暖和呀。
家小,人多,我们全家七口晚上就拽着三张黑蓝的粗布被子,拥拥挤挤在这一条小小的土炕上。怕挤,有时,我们姊妹就一个头朝上一个头朝下插着睡。实在不想这样挤,因为好多次睡着睡着我就被挤下冰冷的脚头了,我就干脆有准备地睡在靠住窗台的哥姐们的脚下面。新房子那时大概已经盖起来了,但不住,主要是没烧的东西,冬天犹如冰窖。大同,说是煤都,遍地有煤,但那不是普通老百姓的,即使其时煤价便宜,便宜得叫今天的人咋舌,仅三四十块钱一吨,普通人家还是烧不起。我记得有一年过年,父母特别高兴,因为一年结工下来挣了一百多块钱!于是,村民生火做饭烧炕只好多用柴禾。在村里上学时,很多的中午,我都腰里别着砍刀,或提着树铲,到京包铁路线两旁砍树枝,以备冬天烧。但这样的树枝硬柴还是不多。就大多烧那些玉米、黍子等庄稼秸秆。谷子秸秆舍不得烧,它是冬季大牲口吃得主食,能卖钱;高粱秆也舍不得烧,人们用它编席子,补席子。
但是,就因为编补炕上的席子,我出状况了。大约也是快要过年的时候,母亲坐在炕上补席子,我在一边抱着板凳当马骑,嘚嘚嘚,嘚嘚嘚地跳。正玩得高兴,突然竟越过炕沿,跌翻到地下。可巧,我的后脑勺就插进地下竖着的粗大铸铁炉钩上,我一下不省人事,几乎要死掉。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,我的记忆完全空白。母亲因此总是特别心痛我,关照我。后来经常抚着我的头,我孩长我孩短地自责。
我绝不怪怨母亲。我小时候太猴。因为有了母亲的悉心照养,我才能像现在这样很好地活着。那时,多少个晚上,我就是枕着母亲轻轻淡淡而意蕴悠长的讲述,酣酣地进入了梦乡……多亏母亲这样的讲述,不,更像是一种传训,让我心中渐渐“长了牙”——人,必须努力,要强。这也大约是父母给取大名的来由吧。
晚上,我们都不愿继续看电视晚会,依旧早早在热炕上睡了。老母亲为了我们回家过年,已经忙碌准备了好多天了。熟的生的荤的素的,该熬的熬了,该煮的煮了,该切的切了,该洗的洗了,我们回家只是吃现成来了。母亲跟邻居曾亮嫂说过,即使子女们回来都下手做营生,不需要她多干活儿,她的身子还是困疼得厉害,好多天都缓不过劲儿来。我完全理解。稍稍干点什么,四十来岁的我都感觉身乏神困,何况年近八旬的老母亲。但初二一大早,习惯早起的我一醒来,母亲马上就拉着了灯。她已经披衣坐了起来,温柔的眼光在我的一家人四口人的身上来回逡巡,摩挲。我看看表,才五点多,就劝母亲再躺会儿,躺在热炕上好好解解乏。母亲却笑笑,说,不乏,不乏,睡不着了,你们睡你们的。
真是好炕啊。妻子惺忪着眼,突然也醒了,这段时间她带着学艺术的女儿太原大同来回跑,的确劳累。她对母亲歉意地笑着说,暖烘烘的都不想醒,也不想起了!
那就多睡会儿!母亲宽容而理解,一脸慈祥。
我忽然就想起曾经的过去,大约也是这种黎明睡不着的时候,母亲总给我讲述她的家族和她的亲戚家族的故事。那些洇湿多年的记忆,都快要风干了。我请求母亲再讲讲,尤其是她的那些读书的表兄弟们,给我提供些写作的素材。母亲马上沉浸在淡淡的兴奋之中。她的记忆是那样清晰,她的姥爷,她的舅舅,和她一块玩耍过的那些表兄弟等等,她都能一一叫上名字,而且,几乎都知道他们在遭遇动荡“年馑”之后的下落。母亲劫后余生般地说,我的五个表舅有四个是大学生,一个在包头钢铁学院当教授,一个在武汉的一所大学当教授,一个分配在石家庄……那荒唐年月,母亲的姥姥村里不断有人逼问我的表舅们的下落,可谁都不告诉他们。如果那时,表舅们都被弄回村,说不准,他们还不如那个现在在村里的神经受过刺激的楞表舅!唉,那样的社会,那种世道!……今天,多好!
亲情和血脉就在母亲淡淡却动情的讲述中,盈溢了一炕。
我看见,妻子虽然眯着眼,但眼脸一动一动的,她在听吗,还是在想什么?两个双胞胎女儿呢,一向讨厌妻子的唠叨,这会儿,竟也静静地躺在炕上的被窝里,间会儿动动身子,竟像我当年那样,空谷禅音般,聆听……
土炕!啊土炕!我心中的泪水也满炕漾溢着。